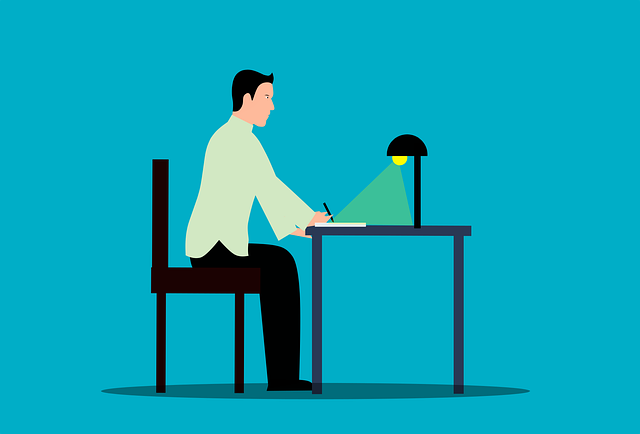如何寫作
當來採訪的人問我,「你是如何寫作的?」通常為了盡量縮短回答的時間,我都會回應,「從左寫到右。」我知道這個答案不盡理想,而且會讓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人感到很訝異。現在我有時間可以好好給個比較仔細的回應。
在我寫第一本小說的期間,我學到了幾件事情。第一,「靈感」其實是狡猾的作者為了讓自己顯得更有藝術才能而使用的糟糕字彙。就如同一句古老格言所說,天才是百分之十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的努力。據說,法國詩人拉馬丁(Lamartine)是如此描述他寫下生涯最好的一首詩的情境:他宣稱,有天晚上他在樹林裡散步時,突然靈光一閃,整首詩就在腦中成形。他過世後,有人從他書房裡發現那首詩的好幾種版本,而且數量驚人,這顯示他花了好幾年時間反覆改寫那首詩。
剛開始時,替《玫瑰的名字》做書評的評論家寫道,這本書是基於一瞬間的靈光乍現而寫成的,不過因為其在概念和語言方面的難度,所以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不過當這本書面臨空前成功,銷售數百萬冊之後,同一批評論家又說,為了讓這本書迎合大眾口味,成為暢銷書,我一定遵照了某種神祕的訣竅來寫作。後來他們還說,這本書之所以暢銷,是因為使用電腦程式寫成的。他們完全忘了,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期,才有堪用的寫作軟體可供個人電腦使用,而當時我的書早已經付印了。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我們所能找到的個人電腦(即使是在美國)是坦迪(Tandy)公司製造的便宜貨,而且除了寫信以外,沒有人會用電腦來寫其他東西。
過了一段時間,那些主張我是用電腦程式寫作的說法使我心煩,我於是製作出以電腦程式寫暢銷書的真正訣竅。
很顯然地,你首先需要一部電腦。所謂電腦就是可以代替你思考的智能機械,這對很多人來說確實是一種優勢。你所需要的只是幾列程式,這一點連小孩都做得到。然後你將數百本小說、科學著作、聖經、可蘭經,還有一大疊的電話簿(這對於為角色取名字很有幫助)輸入電腦裡,以上加總起來大約有十二萬頁的內容吧。然後,使用另一個程式去做隨機排列。換句話說,你將這所有文本內容混合在一起,做一些調整—例如刪去所有包含字母e的字彙—這麼做不僅是為了完成一本小說,也是為了讓小說能呈現佩瑞格式(Perec)的漏字文(lipogram)。接下來,你只要按「列印」即可。而既然你已經刪掉所有含有字母e的字彙了,那麼列印出來的文章一定能少於十二萬頁。
你仔細地檢視這篇文章數次,在幾個最重要的段落底下畫線註記,再來就可以把這些書稿帶去焚化爐燒掉。然後你只要坐在樹下,手上拿著一枝炭筆,以及一疊品質良好的畫紙,讓思緒隨處漫遊,接著你可以寫下幾行文字,例如「月兒高掛空中/樹林沙沙作響」。或許剛開始浮現的文字並不像小說,比較像日本俳句。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開始寫作。
我的靈感姍姍來遲,但我寫《玫瑰的名字》只花了兩年的時間,然而這是因為我不需要做任何有關中世紀的研究。我之前提過,我的博士論文是以中世紀美學為主題,所以我也投注了一些心力更進一步研究中世紀。過去數年來,我造訪了很多仿羅馬式教堂、歌德式教堂等等。當我決定寫小說時,就好像打開一個大櫃子般,裡頭堆滿我這數十年來不斷累積的中世紀檔案。所有資料都已經在我眼前了,我只要選取我需要的即可。至於接下來幾部小說的狀況則稍有不同(雖然我之所以會選定某一特定主題,也是由於我對那個題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的幾本小說都花了不少寫作時間。
《傅科擺》(Foucault’s Pendulum)寫了八年,《昨日之島》(The Island of theDay Before)和《波多里諾》(Baudolino)各花了六年。《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則只花了四年,因為這本書的內容與我小時候在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那時閱讀的書籍有關,我也可以利用堆在家裡的許多舊資料,例如連環圖畫書、錄音帶、雜誌和報紙。簡言之,這些都是我的紀念品與瑣碎物品的收藏,充滿懷舊之情。
建造一個世界
在我孕育下一部作品的期間,我都在做些什麼?我在收集資料。我造訪很多地方,我畫地圖,記錄建築物的設計圖,或是船的設計圖,如同我在《昨日之島》中做的一樣。我也替角色畫肖像畫,寫《玫瑰的名字》時,我替每一個出場的僧侶都畫了肖像畫。我在一座魔法城堡內度過幾年的準備時期—假使你認為這麼說比較妥當,也可以說我是處於孤僻的退隱狀態中。沒有人知道我究竟在做什麼,就連我的家人都不知道。
我給別人的印象是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一直都專注於為我的故事抓取想法、影像和字句。當我在寫關於中世紀的片段時,若我看見有輛車駛過街上,而我對這輛車的顏色印象很深刻,我就會把這個體驗寫進筆記本,或只是記在腦海裡,之後當我想用這個顏色形容某樣東西時(例如細密畫)就會派上用場。
準備寫《傅科擺》時,我曾經好幾個晚上都去逛藝術科技博物館(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一直到閉館為止,因為故事裡有幾個場景就是在這裡發生。為了描述卡素朋(Casaubon)從藝術科技博館到孚日廣場(Place des Vosges)再到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的夜間巴黎散步,有好幾次,我在凌晨兩點到三點間漫遊整座城市,還帶了個小型錄音機記下我沿路看到的各種景色,免得搞錯了街名和十字路口的位置。
我準備寫《昨日之島》時,很自然地去了南太平洋,造訪故事發生的確切地點,我觀察海水和天空一天之內不同時刻的顏色變化,以及魚兒和珊瑚礁所染上的淡淡色彩。
不過我也花了兩三年研究那個時代船隻的設計圖和模型,了解客艙和隔間的大小,並確認一個人要怎麼在船的各區域之間來回。
《玫瑰的名字》出版後,第一個提出改編電影提案的導演是馬可.菲萊利(Marco Ferreri)。他告訴我,「你的書好像是特意寫得像電影腳本的,因為對話的長度都恰到好處。」剛開始我不了解他為什麼這麼說,然後我想起來,我真正開始動筆前,我畫了數百張迷宮和修道院平面圖,這樣我能才知道,當兩個角色從一處走到另一處時會花上多少時間,一邊走路時他們可以說多少話。因此,我虛構世界的設計圖支配了對話的長度。
藉此,我了解一部小說並非只是一種語言現象而已。詩的文字之所以難以翻譯,是因為詩的音韻,以及行文中刻意製造出的多重意義都十分重要,是文字的選擇決定了詩的內容。敘事文卻是相反的狀況,是作者所創建的「宇宙」,和發生在這宇宙裡的事件支配了文章的韻律、風格,甚至是文字的選擇。敘事文受到一個拉丁諺語的影響,「把握主題,話語自然從之」(Rem tene, verba sequentur)。詩則正好相反,「把握話語,主題自然從之」。
最重要的一點是,敘事文是宇宙等級的事件。為了講述某件事,你必須像個造物主般創造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必須盡可能造得準確,如此你才有把握自在穿梭其中。
我一直都嚴密地遵守這個原則,例如,《傅科擺》中,我提到馬弩奇歐和葛拉蒙出版社(Manuzio and Garamond)是位於兩棟相連的大樓內,而兩棟大樓之間有個聯絡通道,我花了很長時間畫大樓平面圖,試圖搞清楚這個聯絡通道應該是什麼樣子,為了配合兩棟大樓間樓層的高低差異,是否需要在裡頭加上一些階梯。小說中我簡短提及了階梯的事情,而我想大多數讀者都沒注意到這一點,就這樣看過去了。但對我來說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沒有好好設計聯絡通道,我就沒辦法繼續寫故事了。
有人說,盧奇諾.維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拍電影時也會做同樣的事。若腳本提到有兩個角色在討論一個珠寶盒的事情,即使電影裡從未打開這個珠寶盒,他也堅持盒子裡要放進真的珠寶,否則演員的表演就會少了那麼點說服力。
我不認為《傅科擺》的讀者應該要知道出版社辦公室的確切平面圖。雖然對作者來說,小說世界的結構(故事裡發生事件和角色活動的場景)是最基本的事項,但對讀者來說,他們通常不會知道微小的細節。可是在《玫瑰的名字》,書的一開頭我就給了一張修道院的平面圖。這是參照過去老派偵探小說的小玩笑,那些偵探小說通常會附上犯罪現場(像是牧師宅邸或領主莊園)的平面圖,此外,也是某種對「現實主義」的嘲諷,作為證明這個修道院真實存在的「證據」。但我還是希望讀者可以想像書中角色在修道院內是如何移動的。
出版《昨日之島》之後,德國的出版社問我,若書內加上一張船的平面圖,會不會有利讀者閱讀。我手上確實有一張船的平面圖,而且我花很多時間設計這艘船,一如我為《玫瑰的名字》用心設計了修道院。但是依照《昨日之島》的狀況,我希望讀者能跟主角一樣困惑。這位主角在迷宮般的船艙內迷失方向,然後又通常都是銘酊大醉後才開始在船內到處探索。所以我得讓我的讀者感到迷惑,同時我自己要有很清楚的概念,就像我之前說的,船的空間設計必須準確到以公釐為單位去測量。
以上內容由商周出版 授權刊登,未經允許請勿轉載。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自白:艾可的寫作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