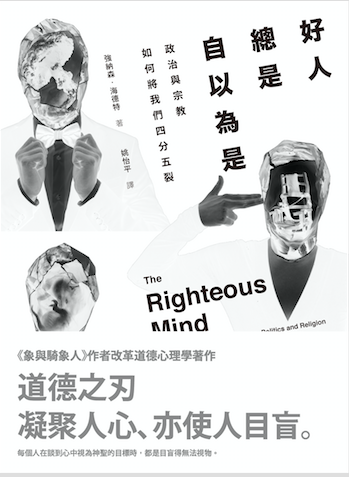直覺的狗和牠理性的尾巴
心智分成好幾個部分,有時會相互矛盾1 ,這是心理學領域的其中一個重要真理。生而為人,就是會感覺到自己被拉往不同的方向,因自己沒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行動,而感到詫異,有時甚至是恐懼。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生活的年代,大家都以為疾病是膽汁不平衡所致。不過,奧維德深諳心理學,他筆下的人物悲嘆:「一股奇妙的新力量牽引著我往前,欲望和理性各自拉扯著我往不同的方向去,我明明看見正確的道路,也認同要往那裡去,卻走上了錯誤的道路。」2
古代的思想家留下諸多隱喻,供後人瞭解這樣的矛盾衝突,然而少有隱喻能像柏拉圖的《提邁歐斯》(Timaeus)對話錄那般活靈活現,書中的敘事者提邁歐斯解釋天神如何創造宇宙,人類也包括在內。提邁歐斯說,有一位完美的造物主只創造完美的東西,祂創造靈魂去填滿新的宇宙,而在靈魂的裡頭,哪有什麼會比完美的理性更完美的呢?造物主在創造了大量完美又理性的靈魂之後,決定休息一下,把剩餘的創造工作交給一些神力較低的神祇,眾神便盡全力勾勒出這些靈魂的血脈。
眾神開始把靈魂裝進最完美的形狀——球形,於是人類的腦袋才多少有一些圓圓的。然而,眾神不久就發現一點,地球表面不平坦,球形的腦袋有點難以四處滾動,而且看起來也不光彩。於是,眾神創造身體來扛腦袋,還把第二個靈魂放進身軀裡。第二個靈魂既不理性又無法永生,實在劣等多了。第二個靈魂的裡頭包含了——
一些可怕又必要的滋擾成分:首先是享樂,這是最強大的邪惡誘惑;其次是痛苦,會使我們逃離善;此外,還有魯莽和恐懼,伴隨旁邊的愚蠢──這是兩者的顧問;接著還有難以平息的憤怒、易入歧途的期望。眾神把前述的成分混合了不理智的感官知覺和大膽妄為的性欲,依其必要,創造出凡俗的靈魂。3
享樂、情緒、感官⋯⋯全都是必要之惡。眾神想讓神聖的腦袋離激動的身體及其「愚蠢的顧問」遠一些,於是創造了頸項。
創世神話多半以部落或祖先作為創世的核心,因此柏拉圖的《提邁歐斯》把中心位置讓賢給心理機能,看來實在奇怪。不過,等你明白了這位哲學家的神話其實提高了哲學家的地位,就不會覺得奇怪了。這則神話證明了哲學家終生擔任理性主教或公正的哲學家皇帝,實為正當。理性派最大的夢想就是「熱情即為且應當只能為理性的僕人」,這種說法顛覆了休姆的表述。
此外,為了避免柏拉圖對熱情的輕蔑受到質疑,敘事者提邁歐斯還說,凡懂得控制情緒之男子,即能終生保持理性及正義,將重生於天堂,獲得永恆的快樂;然而,受制於熱情之男子,來世會轉生為女子。
數千年來,西方哲學向來崇尚理性,厭惡熱情4 。柏拉圖、康德、柯伯格,一脈相傳。本書把這種崇敬理性的態度稱為理性派的迷思。之所以稱為迷思,是因為一群人要是把某個東西給神聖化,這教派的成員就沒有能力對那個東西做清晰的思辨。道德凝聚人心,卻也令人目盲。忠實的信徒會創造出其所篤信卻不符現實的幻想,最後會有人把寶座上的偶像給打下來。前述文字為休姆的主張及其瀆神的哲學看法——理性只不過是熱情的僕人5 。
湯瑪斯.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針對理性與情緒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一種更平衡的模式。一七八六年,哲斐遜擔任美國駐法大使期間,墜入了愛河。哲斐遜經由一位共同友人的介紹,認識了英國藝術家瑪利亞.柯斯韋(Maria Cosway),二十七歲的柯斯韋美麗動人。兩人一見鍾情,幾個小時難分難捨。在那完美的晴日,兩位異鄉人漫步於巴黎街頭,攜手共賞宏偉壯麗的巴黎城。哲斐遜編了個藉口,派信差去取消晚上的聚會,好讓白日的快樂延續到晚間。柯斯韋已經結婚了,但她的婚姻似乎是政治聯姻。這段情在後續的數週究竟進展到何種程度,歷史學家並不清楚6 。後來,柯斯韋的丈夫堅持帶妻子返回英國,獨留哲斐遜傷心欲絕。
哲斐遜為求減輕痛苦,寫了一封情書給柯斯韋。信中運用文學手法,掩飾寫情書給已婚婦女的不當之舉。信中內容是哲斐遜的腦和心在交談,對於是否應追尋一段終將結束的「友誼」而爭辯不休。哲斐遜的腦袋是柏拉圖哲學理想中的理性,腦責罵心,說心竟又拖著腦一起陷入可怕的困境。心乞求腦的憐憫,腦卻回以嚴厲的告誡:
這世上的每樣東西都是加加減減的計算。因此,應謹慎行進,平衡就掌握在你的手中。把一物帶來的愉悅放在天平的一端,也要把隨後而來的痛苦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再看看哪一端佔優勢。7
心一次又一次忍受著腦的辱罵,態度相當順從。最後,心終於鼓起勇氣為自己辯護,並且把腦放在適當的位置,亦即負責處理那些不牽涉到人的問題。
自然之母令我倆住在同一處,卻是在一個分裂的帝國裡。自然之母把科學的領域分派給你,把道德的領域分派給我。若要計算圓形的面積,或是描摹彗星的軌道;當要找出能承受最大重量的拱形物,或最小阻力的固體時,把這些問題扛起來,這種事就交給你吧。畢竟那是你的領域,自然之母並未賦予我那般的認知能力。
同樣的,自然之母並未賦予你同情、仁慈、感激、正義、愛、友誼等感覺,你可不受這些感覺的控制。自然之母令心的機制適應這些感覺。就人類的幸福而言,道德至關重要,不能冒險放在腦袋裡那些不明確的組合上。因此,自然之母令道德奠基於感性,而非科學。 8
於是,現在有了以下三種心智模式:柏拉圖說,理性應當成為主宰,即使唯有哲學家才有能力善加掌握理性,也只能如此9 ;休姆說,理性即為且應當只能為熱情的僕人;哲斐遜提出了第三個選項,理性和感性即為(且應當)各自獨立卻又共同統治,有如羅馬的帝王,把帝國分成東西兩半。究竟誰的主張才是對的?
威爾森的預言
柏拉圖、休姆、哲斐遜都在試圖瞭解人類心智的構成,可惜少了達爾文演化論的幫助,演化論可是瞭解生物構成的史上最強工具。達爾文之所以著迷於道德領域,是因為生物間的合作範例都必須符合達爾文極為強調的競爭和「適者生存」的概念10 。關於道德可能的演化方式,達爾文提出了一些說法,而這些說法多半是說情緒(如同情)促成演化的發生。
達爾文認為,情緒是社交本能的「基石」11 。此外,達爾文還在文中討論了羞愧和驕傲的感覺,兩者皆涉及了人類對於博得好名聲的欲望。達爾文對於道德是抱持先天論,他認為天擇使得人類的心智預先裝載了道德情緒。
然而,隨著二十一世紀道德學的發展,有兩波道德主義浪潮改變了道德學的路線,使得先天論成了一種觸犯道德的主張。第一波的浪潮是人類學家和其他人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心生恐懼所致。社會達爾文主義衍生自達爾文的觀點,但達爾文本人並未表示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最富裕與最成功的國家、種族、個人,才是最適合生存下來的。
因此,施捨窮人,使窮人得以繁殖,即是干涉了演化過程的自然進展12 。至於某些種族先天就比其他種族更加優異之說法,之後也獲得希特勒的擁護。從這個脈絡下來,希特勒支持先天論的話,就表示支持先天論炊H都支持納粹主義了(這個結論不合邏輯,可是如果你不喜歡先天論,在情緒上就說得過去了)13 。
第二波的道德主義浪潮就是邀進政治主義,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橫掃歐美和拉丁美洲境內的大學院校。激進改革者往往想要相信人類的天性是一張白紙,可以在白紙上描繪任何一種烏托邦版本。舉例來說,假使演化過程賦予男女不同的欲望和技能,那麼先天論肯定是錯誤的(同樣的,這種說法在邏輯上存有謬誤,可是這就是正義之心運作的方式)。
認知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一九七○年代是哈佛大學的研究生,他在二○○二年出版《心靈白板論:現代人怎樣剝奪人性》(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說明科學家如何背離科學價值,藉以繼續忠於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科學家變成了階梯教室裡的「道德暴露狂」,他們把科學家同僚給妖魔化,他們鼓勵學生評估概念時,並不是為了真相,而是看那概念是否符合進步主義的理想,例如種族平等、性別平等14 。
最能清楚證明背離科學價值之例子,莫過於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遭受攻訐一事。威爾森終生投入螞蟻和生態系統之研究,一九七五年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探討天擇——無疑是塑造了動物的軀體——如何塑造動物的行為。這個主張並不會引起爭論,可是威爾森竟在末章大膽提議,說天擇也影響了人類的行為。威爾森認為,人類天性確實存在,而且人類在養育子女或構思新的社會制度時,天性侷限了其所能實現的範圍。
威爾森運用倫理學來闡明自己的論點。威爾森是哈佛大學的教授,跟柯伯格和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是同事,所以威爾森很清楚這兩人對於權利和正義所抱持的理性論觀點15 。威爾森顯然認為,理性派的作為其實是在替道德直覺找出聰明的藉口,而最能解釋道德直覺的就是演化了。人之所以相信人類權利,是因為這樣的權利實際上存在嗎?好比是數學真理坐在宇宙書架上的畢氏定理隔壁,等著柏拉圖那方的理性派發現?還是說,人們讀到酷刑報導,心生嫌惡及同情,因而發明出普世權利的說法,替自己的感受辯護?
威爾森贊同休姆的觀點,威爾森認為道德學家在做的事情,其實是先「問過情緒中心」,然後才編織出藉口16 。威爾森預測,倫理學研究不久就會從道德學家的手中被拿走,並且邁向「生物化」,或者改造成適合新興的人類天性學。而哲學、生物學、演化三者之間的連結,會成為威爾森夢想中的「新綜合理論」範例,日後威爾森稱之為融通(consilience,譯註:字面解作「一致」),亦即多種概念「一起跳躍」,創造出統一的知識體系17 。
(本文授權自「大塊文化」,圖文出處:大塊文化/《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