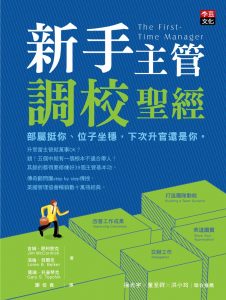接班人就位,堅持理念是場持久戰
第二天上午,我在全錄主管辦公室會見全錄最高階非技術性領導人,最後一位是威爾森本人。我見到的第一位是利諾維茲,就是那位威爾森在一九四六年「暫時」找來幫忙,之後成為威爾森的左右手、一直留在全錄的律師。(全錄成名以後,社會大眾常以為利諾維茲在全錄不只是律師而已,他們常將他視為全錄的執行長。
全錄的主管也知道這項普遍誤解,也不解何以會這樣,因為威爾森無論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之前擔任全錄總裁的期間,或是在之後擔任全錄董事長的期間,一直就是全錄的老闆。)我在利諾維茲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與他會了面,因為他剛奉命出任美國駐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大使,即將離開羅徹斯特與全錄,啟程前往華府履新。
利諾維茲五十來歲,顯得很有衝勁、很精明,而且很誠懇。首先他向我道歉,說他只有幾分鐘時間與我共處,隨即很快便說,依照他的看法,全錄的成功證明自由企業的老理念仍然有效。利諾維茲還說,全錄之所以成功,靠的是理想主義、堅持不懈、勇於冒險與熱情投入等幾項特質。說完這幾句話,他向我揮手道別,走出辦公室。
我留在辦公室裡,覺得自己好像是留在火車月台、剛聽完一位候選人在競選列車後車廂發表演說的小城選民一樣,但如同許多這類選民,我也留下深刻印象。利諾維茲說的那幾句話儘管內容陳腐,但出自他的口中,卻不僅讓人覺得他說的是肺腑之言,還讓人覺得那幾句話是他發明的。我想,威爾森與全錄會想念他的。
彼得•麥考洛克(C. Peter McColough)在威爾森出任董事長以後,繼任全錄總裁,而且顯然有一天會接班成為全錄的老闆(他在一九六八年成為老闆。)我看到他像關在籠中的野獸一樣,在辦公室裡來回踱步,還不時在一個高桌邊停下來寫幾個字,或是對著一台錄音機說幾句話。
像利諾維茲一樣,麥考洛克也是一位自由派民主黨籍律師,不過他生在加拿大。他四十歲出頭,性格開朗、外向,許多人在談到他的時候,喜歡說他是新一代全錄人的代表,負有決定公司未來走向的重責大任。他終於停止踱步,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對我說道: 「我面對成長的問題。」他接著說,想讓全錄在今後出現大規模成長,由於空間不夠,事實上有所不能,而且全錄採取的走向是教育科技。
他談到電腦與教學機器,當他說他「夢想有一種系統,能用它在康乃狄克州寫下一些東西,不出幾個小時就能將這些東西複印,發送到全國各地的教室」時,我的感覺是,全錄的一些教育之夢很可能變成夢魘。
不過,他接著又說: 「精巧的硬體有一種危險,就是它讓人分神,無法全力投入教育。一個機器再精巧,如果你不知道用它來幹什麼,這機器又有何用?」
麥考洛克說,自他在一九五四年進入哈洛伊德以來,他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三間完全不同的公司—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是一家小公司,投入一場危險但刺激的賭博;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是一家成長中、享受勝利果實的公司;現在則是一家朝新方向進軍的巨型公司。
我問他,他最喜歡的是其中哪一家公司,他沉思良久,終於回答: 「我不知道。過去,我覺得工作時比較自由自在,也覺得公司裡每個人在勞工關係這類事務上都有共同看法。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壓力比過去大了,公司也變得更加沒有人味。我不能說日子比過去好過,也不能說日後可能會好過一些。」
在接待人員把我引進喬瑟夫•威爾森的辦公室時,我頗感意外地發現,他的辦公室貼著老式的花草壁紙。統帥全錄大軍的這個人,竟有幾分多愁善感的神采?這似乎是讓我最吃驚的事。
但他有一種坦然樸實、與人無爭的風範,與這壁紙搭配得很好。威爾森個頭不高,年近六旬,在接受我訪談的這段時間,他顯得很拘謹,態度幾近嚴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多少帶一些猶豫。
我問他,當年怎麼會進入家族企業,威爾森回答事實上他差一點沒有這麼做。他在大學主修的第二門課是英國文學,因此他也曾經考慮當個教師,或是在大學擔任財務與行政方面的工作。但在畢業以後,他進入哈佛商學院,成為班上成績最頂尖的學生,就這樣……無論怎麼說,他在離開哈佛那一年加入哈洛伊德,此時他臉上突然堆滿笑容,對我說,就是這樣有了今天。
威爾森最喜歡討論的主題,似乎就是全錄的非營利活動與他的公司責任理論。他說: 「我們這種做法遭到某種怨懟。我的意思是,不僅有些股東感到不滿,說我們揮霍他們的錢—但是這種觀點站不住腳。
在社區裡,雖然你未必會親耳聽到有人這麼說,但有時你憑直覺就能感覺得出他們在說: 『這些年紀輕輕的暴發戶以為他們是誰啊?』」
我問他,那次寫信抗議聯合國電視網節目的事件,有沒有在公司內部造成任何擔憂或膽怯,他說: 「就一個組織而言,我們絲毫沒有退縮。我們全公司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認為這些抨擊只會讓我們更強調我們的重點。
世界合作是我們的工作,因為一旦沒有合作,世界可能不存在,自然也沒有商務可言。我們相信在處理那套系列節目上,我們採取了正確的企業政策,但我不會說那是唯一正確的企業政策。我懷疑,要是我們都是伯奇協會的成員是否還會這麼做。」
威爾森繼續慢條斯理地說道: 「讓公司在重大公共議題上採取立場這件事,會帶來許多問題,迫使我們不斷進行自我檢視。這是一種平衡的問題。你不能對什麼事都無動於衷,這麼做你只會拋棄自己的影響力。
不過,你也不能在每一件重大議題上都採取立場。舉例來說,我們不認為在全國性選舉上採取立場是公司的責任—或許我們走運,因為索爾•利諾維茲是民主黨,而我是共和黨。但像大學教育、民權、黑人就業這類議題,很顯然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希望,如果我們認為應該怎麼做,即使某個觀點不受眾人歡迎,我們也有勇氣堅持這個觀點。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碰上這種情況,那就是我們心目中的社會責任與良好的商業政策發生衝突。
不過,這樣的時間點有可能來到,我們很可能有必要親上火線。舉例來說,我們默默地採取了一些行動,教育一些黑人青年,讓他們可以擔任清掃地板這類活動以外的工作。這項計劃需要我們工會的全面支持,我們也獲得了這些支持。不過,我透過一些微妙的方式知道,這項計劃的蜜月期已經過去,有人在暗中進行抵制。
有些事情正在醞釀,如果讓它鬧大,可能會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業務難題。如果反對者不是幾十個人,而是幾百個人,事情還可能演成一場罷工。一旦發生這種狀況,我希望我們與工會的領導人,還能夠堅持立場盡力一搏。不過,我真的不知道。碰上這種事情,你真的沒辦法預測你會怎麼做。我只是認為,我知道我們可能該怎麼做罷了!」
之後,威爾森站起身走到一扇窗邊說,根據他的看法,公司現在必須做的一項重大工作,是維護公司賴以成名的個人與人性特質,而且這項工作在未來可能更加重要。他表示: 「我們已經看到公司正在逐漸喪失這種特質的跡象。我們正設法向新進員工灌輸這種觀念,不過公司現在在西半球各地擁有兩萬名員工,和過去只在羅徹斯特雇用一千人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我來到窗邊,與威爾森站在一起,準備告辭。就像早先有人對我說的,羅徹斯特在每年這個時候的天氣一樣,這是個濕冷、陰暗的早晨。我問威爾森,在這樣一個陰霾的日子,他可曾有過舊有特質能否維護的疑慮?他點了點頭說: 「這是一場持久戰,我們能不能取勝還不一定。」
(本文授權自大塊文化,出處:大塊文化/《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