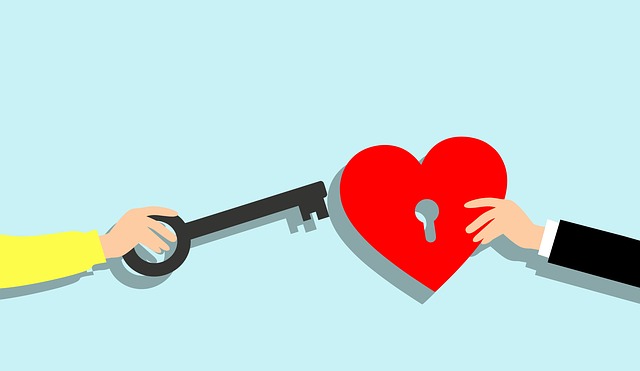山脇開著警車在市內巡邏,神足坐在旁邊。
時間是晚上九點多,車頭燈照亮了前方狹窄迂迴的農業道路,這一帶還維持著開發前的老樣子,有一大片農田,還有搖搖欲墜的倉庫般的木造房子。房門前杮子樹的枝椏伸得長長的,鮮豔的柿子結實纍纍地掛在樹梢,映著車燈。
「天氣越來越冷了。」
「就快十二月了嘛。」
「那個男的不知道怎麼樣了。」
「你是說那個醉漢嗎?」
「是啊。我以為他六十多歲了,沒想到才五十幾。被公司裁員,去找工作卻找不到,被老婆痛罵,自暴自棄,藉酒澆愁……看著連我也感傷起來了。」
「是啊。」
山脇雖然口頭附和,但並不是真的有同感。他畢竟還年輕。
無線呼叫聲響了。神足拿起無線對講機,警車內頓時充滿了緊張氣氛。山脇不禁用力握住方向盤。
「巡邏車二號,巡邏車二號,請說。」
「疑似發生傷害事件。現場是幸福之丘第五區第七棟一○三號。二十一點二十分通報一一○,男性,姓名不詳。據報有人持刀傷人。請立即趕往現場,向報警人了解情形,掌握狀況。一一○受理編號XXX。」
「了解。巡邏車二號即刻前往幸福之丘第五區第七棟一○三號。」神足放下無線電。
「幸福之丘第五區第七棟一○三號,有人報警說持刀傷人,不知是不是肇事者本人。」
「是。」
山脇按下警笛的自動鈕,警笛聲劃破了黑暗,他重重踩了油門。
幸福之丘第五區,是昭和五○年代至六○年代(約一九七○後半到整個八○年代)期間開發出來的社區。住宅樓高僅五層樓,並非高樓建築。全數為出售而非業主專營出租的賃貸類型。居民當中有居住已久的,但經過買賣、房屋所有人出租等等,以新來的居民居多,至少有半數都換過人了。
一○三號住的是誰呢?山脇試著從平日的巡邏中回想,但沒有想出任何面孔。
駛過農業道路,來到國道十六號。大馬路上是一家家複合式餐廳和家電量販店。都是一些以開車族為主要客層的大型店舖。最近郊外的景色千篇一律,甚至經常令人不知道置身何處。大型店舖色彩強烈的招牌招搖地朝馬路突出,原本恬靜的風光頓時變得殺氣騰騰。
最近葬儀社的招牌變多了,顯然城市的高齡化衍生了這項需求。
「那邊右轉。」
「是。」
山脇打了方向盤。
警車從國道轉入一般道路。短短的坡道兩旁種了櫻花樹,但如今卻空留枯枝。
爬完坡,眼前便是一大片社區。這麼多相同形狀的建築聚在一起,不迷路也難。喝醉了回到家,常會錯按別人家的門鈴。每個月他們總會接到幾通有可疑人士按鈴的一一○通報電話,但大多都是醉鬼的傑作。這裡的住宅總共約有七千戶。山脇關掉警笛。
「第七棟。」
他在神足的指示下,正確前往第七棟。接獲一一○通報時,最重要的是盡快趕到現場。山脇與神足正確地掌握了這個社區各棟大樓的位置。平常警察的巡邏並非漫無目的,像這種時候,就能試出平時活動的成果。
警車開在社區內狹小的道路上。道路兩側是一排排同樣規格、同樣大小的建築物。儘管認為何妨蓋點不一樣的建築物,增加變化,但這想必是以效率為目標的結果。這個社區建造時日本還在成長當中,當時為了成長,一定凡事都講求效率吧。
警車在社區內的道路上減速。開車必須小心,因為可能會有人突然衝出來。燈光照亮了社區建築的側面,「7」這個號碼清晰可見。山脇把警車停在第七棟前。
神足拿起無線電,報告「巡邏車二號,抵達幸福之丘第五區第七棟。二十一點二十五分,前往現場。」
「走。」
「是。」
山脇和神足下了車。目前狀況不明。因為有人持刀傷人,山脇不禁感到緊張,伸手摸了摸腰間的NEW NAMBU M60手槍的槍套。
一○三號室就在樓梯旁,屋裡亮著燈,燈光透過陽台照亮了庭院。這裡的一樓是附帶庭院的,院子裡沒有垃圾或落葉。鋪著草皮,但因為季節的關係有些枯萎。朝院子延伸出來的陽台上有空盆栽,白色塑膠製的,好幾個疊在一起,規規矩矩,整整齊齊,彷彿展現了這家人的個性。到了春天,這些空盆裡就會種起花朵吧,但現在空得令人感到有寒意。
面向庭院的窗戶窗簾是拉上的,無法窺見屋內的狀況,絲毫不見人影。
「從大門進去。」神足說。
「希望門沒鎖⋯⋯」山脇回答。
「大門不行的話,就只能從陽台的玻璃門破門而入了。」山脇跟著神足走向大門。
「讓我來。」山脇搶上前。不難想像可能會發生突發狀況,危險必須由年輕的自己來扛。
他先看門牌,「押川」。他想起來了,是一戶有殘障兒子的家庭。走近大門,伸手抓住門把緩緩轉動,門把順勢跟著轉動。
「門沒鎖。」山脇看著神足。
「進去吧。」神足以嚴肅的表情點點頭。
他們悄聲打開了門。「押川先生,押川先生,我們是警察。」
從門縫往屋內看,玄關擺著鞋子,有男鞋、皮鞋,還有運動鞋。也有女性的鞋子,不是高跟鞋,是實穿的低跟鞋。
「啊!」山脇不禁叫出聲來。
「怎麼了?」神足從他身後問。
「看得到人的手,好像倒在地上。」看得到人的手,一個倒在地上的人伸出來的手。
「什麼?快開門!」神足大聲下令。
「是。」山脇猛然把門整個打開,進入屋內。
一名男子俯臥著。他手裡握著聽筒,那隻手滿是鮮血。血流了不少,手臂上也有。仔細一看,玄關和門的內側也沾了血,看來是這名男子打開門鎖的。不知道是死是活。
「這個人交給我,山脇你去看裡面。」
「是。」
山脇聽神足的吩咐,沒脫鞋便直接進入室內。玄關上來的穿堂直接通往廚房兼餐廳,看得到餐桌椅,血是從那邊一路蔓延過來的。山脇小心走著,盡量不踩到血。
身後傳來神足呼喚男子的聲音:「還有氣。喂,你還好嗎?」男子似乎還活著。神足以隨身的無線電請求救護車支援。
山脇循著血跡,來到房門前。血來自這個房間,房門是拉門。他小心翼翼地推開拉門。燈是開著的,這個房間的外面就是陽台。照射到外面的亮光原來就是來自這個房間的燈光。
映入眼簾的首先是被窩。這是個和室,看樣子是寢室。裡面一點聲響都沒有。山脇把拉門整個推開,房間裡鋪著棉被。
一瞬間,他愣住了。腳邊有一攤血。是那名男子的血嗎?
房裡鋪了兩床棉被,棉被隆起成一個人型。裡面有人嗎?被子上並沒看到血。
山脇掀開棉被,被窩裡是一個仰臥的女子,中年女子。是男子的妻子嗎?枕著枕頭的頭顱四周形成了血池。大量的血滲透了床單被褥,染成了深紅色,血多得彷彿像是從底下汩汩冒出來似的。血是從脖子流出來的,她的脖子被刺傷了。
另一床棉被也是隆起的。山脇推測應該就是那個殘障的兒子,他曾看過兒子和母親一起在庭院裡。他向他們打招呼,兒子報以溫柔的笑容。雖然是唐氏症特有的表情,但那坦然的笑容宛如天使。兒子的體格比母親還高大,很胖。從外表看不出年齡。光看臉覺得年幼,但從體格判斷應該已經成年。
山脇掀開了另一床棉被。
裡頭正是那個曾經對他報以溫柔笑容的年輕男子,是這家的兒子沒錯,但浮腫的眼皮是閉起來的。和母親一樣,脖子被利刃所刺。從傷口流出來的血,擴散到枕頭和墊被。
兩人都沒氣了。山脇朝著在玄關的神足喊:「有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遇刺。很遺憾,都身亡了。」
*
醫生說,健太只能活到兩歲。他無法自行喝奶。由香里擠出自己的母奶,裝進奶瓶,拚命餵健太。
孩子只能活到兩歲。在那之前,我們合力養育健太吧──由香里這麼說。我們根本沒想到,養育一個活不了的孩子是個矛盾。健太生病的時候,由香里一整晚看護著他。健太病好了,由香里卻累得像老了好幾歲。我們過的就是這樣的日子。
從未體驗過親情的我,比任何人都嚮往家庭的溫暖。我這個父親去工作,當家庭的支柱。妻子守在家裡。孩子在父愛母愛中開朗、健康、聰明地長大。我心目中的家庭是這個樣子的,一個充滿笑容與歡樂的家庭。
可是,現實卻非如此,有的只有沉重的嘆息和疲勞。這孩子如果正常的話……我一直無法甩開這種想法。
「即使長大,也會伴隨著重度的智能障礙,他的發育會比一般孩子晚很多。因為心臟不好,所以活不久,頂多到兩歲。請你們好好愛他。」醫生苦澀的話在我腦海中重播。
不管是翻身還是走路,健太都比其他孩子慢。比較沒有意義,但無論如何就是會比較。啊啊,為什麼不會走?啊啊,為什麼不會說話?怎麼不會叫爸爸、媽媽呢?
健太這個看不到將來的孩子,不如就像醫生說的那樣,兩歲就死掉吧──我曾因為發現自己竟像個惡魔般如此期待而驚懼不已。
想一想,健太真可憐。死了還比較幸福吧!儘管別人會這樣想,健太還是長大了。
我希望健太早點死嗎?我不知道。咦,你不知道?答案明明就在你心裡啊,怎麼可能不知道。你其實巴不得健太早點死。你把孩子有唐氏症這件事瞞著你服務的信用金庫,就是最好的證明不是嗎?這不就等於否定了健太的存在嗎?
你曾經和信用金庫的上司商量過健太的事嗎?你瞞得滴水不漏是為了什麼?事件發生之後,大家知道我有唐氏症的孩子一定很驚訝。你隱瞞是因為你認為有個有障礙的孩子,會影響自己的晉升和評價嗎?
在調動方面的確需要公司的體諒,也的確會對評價有所影響吧。但是,我在信用金庫裡評價本來就不高了。讓我當業務我也做不好,總是很陰沉,不知道在想些什麼。行政文書的工作我處理得一絲不苟,所以我一直當內部文書工作的管理者,但也沒有什麼發揮領導能力的地方。就只是個會把文書作業處理得正確無誤的人。這就是公司對我的評價。
從小受到父母虐待、輕蔑、忽視的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退縮的生活方式,只求不突出、不挨罵。就算我明知這樣不行,還是會變成這樣。在職場上,結果還是一樣。我曾經一度調到業務部門,卻有一次不小心忘了和客人的約定。當時,客人來投訴,上司把我狠狠罵了一頓,就像那個繼母一樣。我從此就退縮了,本來陰鬱、沉悶的評價就已經夠差了,這下變得更差。
在職場上,我在也等於不在。這樣的我,就算說出了有唐氏症的孩子這件事,上司也只會應一聲「喔」吧。他們才不會去了解唐氏症,也壓根兒不會想知道那對家庭生活會造成什麼影響。
至少會寄予同情吧?可是,被上司和同事同情有什麼用?我的家庭必須由我來保護。你是不是認為陰鬱的原因是健太?你從來沒有想過只要健太不在,你應該會開朗一點嗎?
健太不斷成長。相信醫生說他兩歲會死的我,在健太超過兩歲時,感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絕望,因為我驟然失去了目標。就是因為我相信神給了我他兩歲就會死這個絕對的答案,我才能克服懷著希望養育一個無法指望將來又沒有希望的孩子的矛盾。在那之後,我就可以重新建立一個開朗、平穩、充滿希望的家庭。我是這樣相信才努力熬過來的。我也協助了由香里。
健太兩歲的生日,那就是他死的日子,雖然對不起他,但也是我重新建立家庭的日子。然而,健太卻平平安安地活過了那一天。而且連爸爸、媽媽都不會叫,不會爬也不會走……
從那天起,我就開始逃避與健太的所有接觸。「我在外面工作,賺錢回來,健太就由妳好好照顧,這是家務分擔。」我對由香里說。由香里說「我知道了。」和我不同,她的個性開朗,也善於社交。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她的神情顯得很悲傷。她是個不會示弱 的人,把鬱悶、委屈留在心裡,把笑容掛在臉上。那時候,她想對我說的應該是「我們一起養育健太吧」。
可是,我再也受不了懷著希望養育一個沒有希望的孩子這種矛盾了。所以我祭出「家務分擔」的大帽子逃避養育健太的責任,就像對我不盡扶養義務的父親一樣。
我想,那是在健太五歲或六歲的時候。因為由香里很忙,由我代替她帶健太去醫院。健太一開始就不願和我一起去。我很久沒有和健太一起外出,所以也不覺得高興。那孩子怪怪的。哦,是唐氏症吧。
四周的竊竊私語傳入耳裡。也許是我幻聽,但忍不住就會朝聲音的來向瞪過去。健太是個靜不下來的孩子。他有過動的傾向,雖然好不容易把他帶到了醫院,但在我辦理掛號的時候,他也在其他門診患者之間跑來跑去。我怕他危險,也怕他打擾別人,片刻都不得安心。
「好辛苦喔。」我一抓住健太的手臂,坐在沙發上的一名女子便以說不出是同情還是憐憫的表情說。
「不好意思。」我行了一禮。
就在這時候,健太放聲哀嚎,聲音大得彷彿能震動無數片玻璃,我不禁雙手捂住耳朵。坐在眼前的女子露出了毫不掩飾 的厭惡神情。
原因好像是我抓健太的手臂抓得太用力了。錯是在我,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丟臉得全身像燒起來一樣發燙。我甩了健太一個耳光,健太凝視著我的眼睛。他的眼神不是平常那種不知道在想什麼的眼神,他有明確的意識,他恨我。
然後,幾百、幾千片玻璃又被震動了。他的尖叫聲響徹了整家醫院,我用力塞住耳朵。上次,那個姓長嶋的律師來了。
「押川先生,同樣有唐氏兒的父親沒有一個人同情你。」長嶋說。
「我也不想要他們的同情。」我說。
「有位專家解釋,殺死健太是終極的虐待。還說,這是因為你在成長過程中受到虐待而造成的負面連鎖。對於殺死你太太和健太,你現在有真心反省嗎?」長嶋說。
殺死健太是虐待?原因是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虐待?我真心反省了嗎?何必問我這些,你到底想要我怎樣?
由香里很痛苦,她苦苦哀求我殺了她,我不能再讓她受苦了。由香里說:「我死了之後,不能留下健太一個人。那孩子沒有我活不下去,讓健太也一起跟我走。」
反省?後悔?絲毫沒有。我是把他們倆從苦海裡拯救出來,那是唯一的選擇。長嶋怎麼可能懂得我和由香里的苦,他怎麼可能懂得把一個沒有希望的孩子當作好像有希望來養的痛苦!
要我說幾次都可以,那是唯一的選擇。快判我死刑吧!
圖文授權自皇冠出版/ 江上剛《愛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