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道歉
試圖解脫難受的罪惡感或羞恥感
當我們體認到自己造成傷害,隨即產生令人難以承受的罪惡感,而這就是延遲道歉的一個常見原因。想想看約翰.普拉莫的例子,他二十四歲,是一名直升機飛行員兼作戰官,在越戰期間負責輔助來協調聯軍轟炸。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聯軍向浪滂縣的村莊投擲重型爆炸性武器與燒夷彈。1次日早晨,美國軍方報紙《星條旗報》登出一則有關該起空襲的報導,其中包含一張如今舉世聞名的照片—年僅九歲的小女孩金福逃離遭烈火吞噬的家園。幾年後,普拉莫「……盯著照片,看見凝固汽油燒光了她的衣服。她瞇緊了雙眼,張大著嘴巴,驚駭莫名,無法理解自己怎麼會遭受這種痛苦。她拍打雙臂,姿態笨拙,彷彿她不認為那是自己的手臂……『我難受得像是膝蓋遭到暴擊。』」
戰後數十年,約翰.普拉莫酗酒成性,經歷了兩段失敗的婚姻,飽受折磨。他最終辭去了國防承包商的工作,轉而成為衛理公會的神職人員。儘管他已投身新的志業,卻仍對深印在他腦海中的那張照片耿耿於懷,一想起它就覺得心痛。3他甚至夢見那張照片,還聽見受害者的尖叫聲。「如果她能凝望我的雙眸深處,普拉莫心想,她會明白我為了自己對她造成的傷害,感到多麼痛苦,多麼悔恨。」
事發經過二十四年後,約翰.普拉莫與金福在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相見,普拉莫這麼描述那次會面:「她朝我敞開雙臂……我卻只能不斷地說:『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而她輕拍普拉莫的背,告訴他:「沒關係,我原諒你,原諒你了。」他們那天陪伴彼此,度過了兩個小時。「自從那天見過金福,我再也沒在睡夢中聽見任何聲音,再也沒有尖叫聲,一切復歸寧靜。」
這段故事闡明了罪惡感導致道歉延遲的情況,在傷害事件發生後二十四年才進行道歉。普拉莫並未遭到控訴,因為受害者當初甚至不知道他的身分。普拉莫沒有試圖操縱情勢或逃避對自身犯行的責罰,他承受的痛苦來自內在—他僅僅是因為內心無法獲得安寧。就他的立場看來,面對面道歉並獲得寬恕,終於平息了那些尖叫聲,使他的心靈平靜。此外別無他法,即使是轉變職業、重新適應生活的巨變,也沒辦法緩解他深植心中的罪惡感。
以罪惡感、羞恥心為動機,並盼望能夠賠罪而延遲道歉的另一段故事,是關於日本情報官永瀨隆,他在二戰期間虐待在桂河強迫服勞役的英國士兵戰俘。戰後,永瀨隆試圖擺脫內心折磨,他書寫當時的經歷,並回到當年虐待戰俘的地點創建寺廟。然而,就如同普拉莫,永瀨隆沒辦法藉由這些「良善事業」來解除心理痛苦。直到事發經過六十年後,他偶然再次遇見當年的其中一名受害者,才給了他直接為罪行道歉的機會。而這名英國士兵艾瑞克.羅麥斯或許是為了寬慰內心報復的激情,交給這名軍官一封信,原諒了他。羅麥斯在自己的書《心靈勇者》中傾訴了這段故事,我們會在第十一章詳盡討論。
在接下來的這個案例中,罪惡感顯然是道歉的動機。一九七六年,在一場反種族融合運輸政策的暴力示威中,數名青少年與年輕人毆打泰歐多.藍茨馬克,他是一名非裔美國人律師,當時正站在波士頓市政廳的臺階上。
不但如此,一名年輕人還拿起美國國旗當做武器,將旗桿朝藍茨馬克瞄準,垂落地面的星條旗微微捲起。史丹利.佛曼便是以照片記錄這個事件,而贏得了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獲獎原因包含了時機(建國兩百週年)、事發地點、美國國旗做為武器的象徵意義突出、受害者的種族、加害者的膚色等等,構成了富有力量的畫面,傳遞出偏執與仇恨的深刻訊息。藍茨馬克先生從未看過攻擊他的人一眼,也沒有逮到任何人。
八年後,其中一名攻擊者博比.鮑爾斯尋訪藍茨馬克先生,「羞愧難當地」向他招認自己是攻擊事件的共犯,並表示希望能向他賠罪。「我不是個惡毒的人,」他解釋,「我老是為了自己的許多問題怪罪運輸政策……但那許多問題其實都是我自己的問題。」鮑爾斯說當時他是絆倒藍茨馬克的那個人,然後他就閃到一邊,好讓那些「走狗」趁機攻擊他。事發當年,鮑爾斯才十七歲,如今他澄清自己並非種族主義者。「我那時只是個憤怒的年輕人,就只是個男孩,真的。」當時鮑爾斯的父親生命垂危,祖母也病了,他也時不時地惹上一些麻煩。鮑爾斯一直覺得人生無法步上正軌,直到他為了所犯的錯誤付出代價。鮑爾斯覺得自己將近二十年來就像穿著「粗麻布衫」,他說:「我知道泰德原諒了我,但我很難原諒我自己。」
鮑爾斯無論是承認(坦白)冒犯行為或是承擔罪責(「我老是為了自己的許多問題怪罪運輸政策……但那許多問題其實都是我自己的問題。」)他的懊悔與痛苦都意義深遠,而他的解釋也相當可信(並非種族主義者,「只是個憤怒的年輕人」,祖母生病,父親性命垂危)。
本文授權刊登自好人出版/亞倫.拉扎爾《道歉的力量:維護尊嚴與正義,進行對話與和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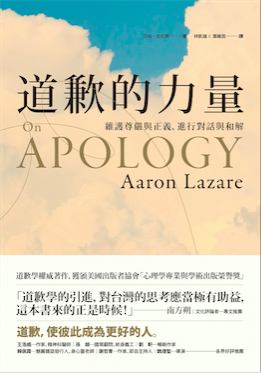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