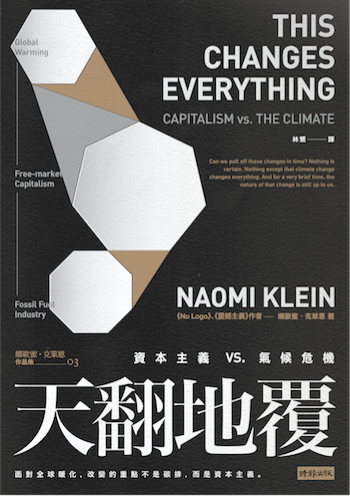引言:是好是壞,一切都在改變
廣播系統傳出聲音:「原定從華盛頓特區起飛,前往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3935班機上的乘客,請您收拾隨身行李,依序下機。」
乘客走下樓梯,聚集在炎熱的停機坪上。他們看見不尋常的事──「美國航空」噴射機的輪子陷入黑色鋪面,彷彿水泥未乾。機輪入地之深,事實上使得前來拖曳飛機的卡車拉不出機輪來。航空公司希望減掉機上三十五名乘客的重量,飛機就會輕得可以拉動。拉不動。有人在網上貼圖:「為什麼我的班機取消了?因為華盛頓特區熱爆了,我們的飛機陷入地面。」
最後,召來較大型、馬力也較強的拖車來拖曳飛機,這次成功了。飛機終於起飛,延誤了三小時。航空公司發言人將此意外事件歸咎於「非比尋常的氣溫」。
2012年的夏天,氣溫的確不尋常的高(跟前一年和後一年一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一點都不神秘,就是因為揮霍無度的燃燒化石燃料,正是美國航空勢必也決意要做的事,儘管熔化的停機坪帶來不便。這樣的反諷──燃燒化石燃料劇烈改變了我們的氣候,以致於妨礙了我們燃燒化石燃料的能力──不會阻止3935班機上的乘客重新登機,繼續他們的旅程。各大新聞媒體報導這件意外插曲時,也都不提氣候變遷。
我沒有立場來評判這些乘客。我們每一位過著高消費生活型態的人,不論恰好居住在何處,隱喻上來說,都是3935班機上的乘客。面對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我們整個文化就是繼續從事導致危機的行為,只不過再加把勁、多費點力而已。如同航空公司招來引擎更強的拖車來拖曳飛機,全球經濟體提高賭注,從傳統的能源化石燃料轉到甚至更骯髒、更危險的替代品──亞伯達油砂提煉出來的瀝青、深海鑽探的石油、水力壓裂法採集的天然氣、爆破山頭開採的煤,等等。
同時,每一場威力驚人的天災製造了層出不窮的反諷畫面,喻示了全球氣候越來越不利於最該為暖化負責的產業發展。例如2013年卡加利(Calgary)發生歷史罕見洪災,迫使開採亞伯達油砂的石油公司高層躲起來,並且遣送員工回家;而我們目睹運送易燃石油的火車,在崩塌的鐵橋邊緣搖搖晃晃。又好比前一年肆虐密西西比河的乾旱,使得水位太低,導致滿載石油和煤炭的貨船好幾天動彈不得,只好等待美國陸軍工兵隊挖開一條通路(而他們必須挪用同一條水路前一年歷史性洪災的重建基金)。或者全國其他地區的燃煤發電廠暫時關閉,因為用來汲水冷卻機器的河川,要不是過熱就是乾涸了(有些例子是又熱又乾)。
生活在這樣的認知衝突中,只不過是身處這個不和諧的歷史時刻,不可避免的一環──當一向刻意忽視的危機迎面而來賞我們耳光時,我們卻加倍下注最初導致這場危機的玩意。
我否認氣候變遷之久,遠超過我所願意承認。當然,我知道正在發生,不像唐納‧川普和茶黨喋喋不休,冬天總是會來啊,證明氣候變遷全是唬人。然而關於細節我始終模糊不清,只是略微掃過大多數的新報導,特別是那些真正駭人的故事,我更不想深究。我告訴自己,科學太複雜了,而且環保人士正在處理。於是我繼續表現得彷彿皮夾中擁有一張證明我是飛行常客的「菁英會員金卡」,沒什麼不對。
我們太多人陷入這種否認氣候變遷的心態。我們觀望那麼一剎那,然後就掉過頭去。或著我們觀望,但是把它變成笑話(「更多末日的徵兆了!」)。這是掉過頭去的另一種方式。
或著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安慰人心的故事──人類是多麼聰明,會創造出科技奇蹟,安全的將碳排出大氣之外,或是神奇的降低太陽的溫度。為寫作這本書進行研究時,我發現這還是掉過頭去的另一種方式。
或著我們觀望,然後試圖保持超理性的態度(「一塊錢就是值一塊錢。聚焦在經濟發展比氣候變遷有效率得多,因為財富是最好的保護,讓我們避開極端氣候」),彷彿當你的城市沉到水面下時,多幾個銅板差別可大了。如果你剛好是位開口閉口政策的專家,這也是一種掉過頭去的方式。
或者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我們太忙了沒法去管這麼遙遠又抽象的事,儘管我們目睹紐約市的地下鐵進了水,紐奧良的民眾站到屋頂上,而且清楚沒有人是安全的,最脆弱的最不安全。而且雖然完全可以了解,這仍然是掉過頭去的一種方式。
或者我們觀望,然後跟自己說,我們能做的就是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靜坐冥想、逛農夫市集、停止開車,卻忘了嘗試去真正改變體系,是這些體系製造出無所遁逃的危機。因為那樣做會帶來太多「負面能量」,而且絕對不會成功。或許乍看之下,好像我們正視問題了,因為林林總總的改變生活方式,的確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然而我們依舊有一隻眼緊閉著。
或者我們的的確確正視了,然後不可避免的,我們似乎忘記了。想起來,又再度忘掉。氣候變遷就是這麼回事,你很難把它放在腦袋裡太久。我們陷入古怪的生態失憶症,想起來、忘掉、想起來、又忘掉……由於各種完全合理的理由。我們否認,因為害怕探究這項危機的完整事實會改變一切。我們是對的。
我們清楚如果繼續目前的行徑,允許碳排放一年一年升高,氣候變遷會改變我們的世界,一切都會改變。主要的城市很可能淹沒,古代的文明會被海洋吞噬;有很高的機率我們的孩子一生大半時間都在忙著逃離猛烈的暴風雨和極端的乾旱,不斷努力從災難中復甦。而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可以迎向這樣的未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什麼事都不做。只要繼續我們目前的行為,無論是信賴科技會解決問題,或是照顧自己的花園,還是跟自己說真不幸我們太忙了沒時間處理。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反應,彷彿這已是一場無可挽回的危機。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繼續否認我們其實是多麼膽顫心驚。然後,一點一點的,我們就會抵達我們最害怕的地方,面對我們一直轉開眼睛不去看的事情。不需要額外的努力。
有方法可以避免這種陰暗的未來,或者至少讓未來不要那麼悲慘。不過弔詭的是這也牽涉到改變一切。對我們這種高消費的人來說,涉及的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經濟活動,甚至是我們如何界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好消息是這許多的改變顯然不會造成災難,也有許多改變簡直是令人興奮。不過長久以來我並沒有發現。
我記得自己不再轉開眼睛,直視氣候變遷這項事實的確切時刻,或者至少我讓眼睛停留了好一陣子。那是在日內瓦,二〇〇九年的四月,我會晤了玻利維亞駐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大使,當時是位年輕得令人意外的女性安潔莉卡˙納瓦羅˙莉亞諾斯(Angélica Navarro Llanos)。玻利維亞是個貧窮的國家,用於國際事務的預算很少,納瓦羅˙莉亞諾斯除了負責對外貿易,最近又多了個官職,掌管氣候相關事宜。在一家空蕩蕩的中國餐廳共進午餐時,她跟我解釋(拿筷子當道具畫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變化軌跡),氣候變遷在她看來既是對她國家人民的嚴重威脅,然而也是機會。
是威脅理由很明顯──玻利維亞非常依賴冰河提供飲水和灌溉用水,而那些高聳於首都上空的群山,白皚皚的山頭以驚人速度轉成灰色和棕色。機會是,納瓦羅˙莉亞諾斯表示,像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幾乎沒做過什麼讓排放量節節攀高的事,既然如此,他們就可以宣稱自己是「氣候債權國」,排放大國有義務提供金錢和技術支援,用來支付處置氣候相關災難所需的沈重花費,同時協助他們以綠色能源來發展國家。
她不久前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上發表演講,闡明各種方式的財富轉移;她給了我一份講稿。她說:「好幾百萬人生活在小島、發展最遲緩的國家和內陸國家,還有生活在巴西、印度、中國,以及全世界的貧弱社區裡,因為不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問題而受苦……如果我們要在下個世代抑制排放量,我們需要召喚超越歷史先例的龐大動員。我們需要為地球制定馬歇爾計畫。這項計畫必須以前所未見的規模進行財力和科技的移轉。我們必須讓每個國家的科技充分發展,以確保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同時,減少排放量。我們只有十年的時間。」
當然,地球馬歇爾計畫經費會非常高,如果不是好幾兆,就是好幾千億美元(納瓦羅˙莉亞諾斯不願意給個數字)。我們很容易想到,光是費用本身就讓計畫無法起步,畢竟,那是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機鬧得正兇。不過撙節的刻苦邏輯──以公部門裁員、學校關閉之類的形式將銀行家的帳單轉嫁到人民身上──還沒有成為常態思考,因此金融危機非但沒有讓納瓦羅˙莉亞諾斯的想法看起來比較說不通,反而有相反效果。
我們都剛剛目睹好幾兆美元到位救援,在菁英階層決定宣布這是危機的時刻。我們被告知,如果讓銀行倒了,整個經濟會連帶崩潰。這是集體存亡的大事,因此一定要找出錢來。過程中,暴露了經濟體系核心中相當大的虛妄層面(需要更多錢?印鈔票!)更早幾年,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政府採取了類似途徑因應國家財政需求。許多西方國家需要在國內建立安全/監視系統,同時在國外打仗,預算似乎從來不是問題。
我們的領袖從來不把氣候變遷當成危機來處理,儘管事實上,氣候變遷的風險是,它摧毀人命的規模,遠遠大過倒閉的銀行或是倒塌的建築物。科學家告訴我們,為了大幅降低災難的風險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卻被當成不過是溫和的建議,行動不妨無限期延後吧。顯而易見,什麼狀況會被宣布成危機不只是以明確事實為根據,也反映出權力和優先順序。但是我們毋須成為旁觀者,不是只有政治人物才有權力宣布危機出現。一般人透過群眾運動也可以宣布危機來了。
奴隸制度對英國和美國的菁英階層而言,不是危機,直到廢奴主義把它變成危機。種族歧視不是危機,直到民權運動把它變成危機;性別歧視不是危機,直到女性主義把它變成危機;種族隔離不是危機,直到反種族隔離運動把它變成危機。
用同樣的方式,如果我們有足夠人停止掉過頭去,決定氣候變遷是危機,值得馬歇爾計畫等級的回應,那麼它就會成為危機。於是政治菁英就必須回應,不只是提供資源,也要改變自由市場的規則──這些規則已經證明了很容易曲解,只要菁英階層的利益面臨威脅。每當危機將氣候變遷推到我們心頭上一陣子,我們偶爾會瞥見這樣的潛在動能。「在救援的努力中錢不是問題,需要多少錢就會花多少錢。」英國首相卡麥隆宣布,在他的國家因為二〇一四年二月的歷史性洪災,好多地方泡在水裡而英國人民因為政府沒有給予更多協助而憤怒時。7卡麥隆本人可是撙節先生呢。
聆聽納瓦羅˙莉亞諾斯描述玻利維亞的前景,我開始了解氣候變遷如何能夠成為增進人類福祉的力量,只要我們把它看成真實的全球性緊急事件,類似那些漲起來的洪水。這股力量不僅可以讓我們安全的避開極端氣候,而且造就各方面都比較安全和公平的社會。迅速棄用化石燃料,為即將到來的惡劣氣候做好準備,需要龐大的資源,然而這筆資源可以幫助一大批人脫離貧窮,提供現在嚴重缺乏的公共設施,從乾淨的水到電力。理想的未來願景不只是要倖免或熬過氣候變遷,也不只是「減緩」和「適應」,如聯合國使用的了無生氣字眼。在這樣的未來願景中,我們集體利用危機,躍向(坦白說)看起來比目前好的處境。
那場談話之後,我發現自己不再害怕埋首於探討氣候威脅的科學事實。我停止迴避相關文章和科學研究,閱讀我搜尋得到的一切資訊。我也停止將問題外包給環保人士;停止跟自己說那是別人的議題、別人的職責。環境正義運動逐漸興起,透過跟其他人對話,我開始從各方面看見,氣候變遷可以成為正向改變的催化力量──成為進步主義者前所未有的最佳論證,要求重新打造和復興地方經濟;從企業腐蝕的影響力中奪回我們的民主制度;阻擋有害的自由貿易新協定,改寫舊的條約;投資在缺錢的公共基礎建設,例如大眾運輸和合宜住宅;拿回能源和水等必要公共設施的所有權;改造我們生病的農業系統,讓它變得健康有活力;打開邊界接納因氣候衝擊流離失所的移民,同時終於懂得尊重原住民的土地權利──上述一切都有助於終止國內和國際上已達荒誕程度的不平等。
而且我開始看見徵兆──新的聯盟和新的論證──顯示,如果各種不同的連結能獲得比較廣泛的了解,那麼氣候危機的急迫性就可以成為基礎,動員出強大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將會把表面上不相干的所有議題,彙整為前後連貫的論述,闡明如何保護人類免於殘酷又不正義的經濟體制荼毒;免於不穩定的氣候肆虐。我寫作這本書,因為我得到了結論:「氣候行動」正好能提供如此稀罕的觸媒。
人民給予的震撼
不過我寫這本書,也是因為氣候變遷同樣可能催化出非常不同,而且不是我們想要的各種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轉型。
我之前花了十五年時間,埋首研究經歷極端震撼的社會──這些震撼來自經濟崩潰、自然災害、恐怖攻擊和戰爭。我深入探究,社會在承受這些巨大壓力的期間會如何轉變。震撼事件究竟是如何改變集體意識,讓人們接受原本不可能的事情?有些是好的改變,不過絕大多數變糟了。如同我在上一本著作《震撼主義》討論過的,過去四十年,企業為追求利益,有系統的利用上述不同形式的危機,強力灌輸讓少數菁英富裕的政策──取消管制、削減社會福利支出,以及力推公共領域的大規模私有化。這些危機也成為藉口,極力箝制公民自由,冷酷侵害人權。
有許多徵兆顯示,氣候變遷也不會是例外──並不是激發出解決方案,讓我們有真正機會免於災難性的暖化,保護我們避開勢所必然的災難,而是再度利用危機把更多資源交付給百分之一的人。你已經見識到這個過程的初期發展。全世界的公有森林變成私有化的林場和保留地,因此地主可以收集所謂的「排碳額度」。這是一場高獲利的騙局,我之後會探討。「天氣期貨」成為新興交易,允許公司和銀行投注在天氣變化,彷彿致命的災難是賭桌上的遊戲。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六年之間,天氣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躍升了將近五倍,從九十七億美元成長到四百五十二億。全球再保公司賺了幾十億的利潤,部分是藉由販賣新型態的保護方案給發展中國家來牟利。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做了什麼事造成氣候危機,但是他們的基礎建設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極為脆弱。
在坦白的時刻,軍火巨擘「雷神」(Raytheon)解釋道:「因應氣候變遷而改變的消費行為和需求,很可能帶來擴大的商機。」這些商機除了私人救災服務之外,還包括「需求它的軍事產品和服務,以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乾旱、洪水和暴風導致的安全顧慮。」9每當有人質疑氣候危機是否真的如此迫切時,我們可不要忘了:私人的自衛隊早就動員了。
除了配槍的需求逐漸升高,乾旱與洪水創造了各式各樣的商機。二〇〇八到二〇一〇年之間,至少有兩百六十一件專利申請是關於栽培「能夠調適氣候」(climate-ready)的作物──也就是據信可以耐受極端氣候的種子。這些專利將近百分之八十是由六家大型農企業財團掌控,包括孟山都和先正達。而同時超級颶風珊迪讓美國紐澤西州不動產開發商大發利市,他們獲得好幾百萬美元在損傷輕微的區域蓋新建築,而住在嚴重受損的公共住宅的居民,卻一直活在夢魘之中,差不多就是卡崔娜重創紐奧良之後上演的相同劇碼。
這一切都沒什麼好吃驚的。我們目前的體制就是打造來尋找新方法,將共有財私人化,並且從災難中獲利。放任這個體制自行其是,也成就不了其他事。然而「震撼主義」並非社會回應危機的唯一方式。二〇〇八年肇始於華爾街的金融崩潰震盪了整個世界,也讓我們見證了近年來的其他發展。突然攀升的食物價格為「阿拉伯之春」創造了條件;撙節政策激發了群眾運動,從希臘到西班牙、到智利、到美國、到魁北克。我們許多人越來越善於對抗那些蔑視道德利用危機掠奪公共領域的人。然而那些抗議也顯示出,光是說「不」是不夠的。如果反對運動想要更多的成果,而不只是鬧個轟轟烈烈然後能量耗盡,那就需要有全盤的願景,看清楚應該用什麼來取代我們失敗的體制,還有為了達成目標需要採取的嚴肅政治策略。
進步主義者曾經知道該如何行動。在歷史上大規模的危機中,「人民至上」的民粹主義者多次贏得社會與經濟正義的大勝利,最著名的包括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之後的「新政」,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誕生的無數社會計畫。這些政策廣受選民歡迎,制定成法律並不需要我在《震撼主義》一書中記錄的獨裁伎倆。成功的要素是建立起強壯有力的群眾運動,能夠對抗那些捍衛失敗現狀的人,同時明確要求每個人都可以較為公平的分享經濟大餅。這些特殊的歷史時刻猶有遺澤(儘管四面楚歌),包括:許多國家的公共醫療保險、老人津貼、住宅補貼,以及公共資金贊助藝術。
我深信氣候變遷提供的歷史機會,規模更為宏偉。為了達成目標,將碳排放減量到諸多科學家建議的水準,我們將再度擁有機會推動前瞻性的政策,大幅改善生活品質,縮短貧富差距,創造大量優質工作,同時從根做起重新活化民主制度。跟「震撼主義」的終極表現──瘋狂掠奪新資源和鎮壓──大異其趣,氣候變遷可以是人民給予的震撼,由下而來的一擊。我們可以將權力分散到眾人手裡,而不是由少數人掌握;徹底擴大公有財,而不是支離破碎拍賣掉。當右翼震撼專家利用真實和製造出來的緊急狀況,推動使危機更加迫近的政策時,本書所探討的各種轉型將會反其道而行──追究最初讓我們面對一連串危機的根本原因,同時讓我們擁有比較適宜生活的氣候而不是我們正要栽進去的極端氣候,並且營造出比較合乎公平正義的經濟,遠勝過我們目前的經濟體系。
不過在這些轉變能夠實現之前,在我們願意相信氣候變遷可以改變我們之前,首先我們必須停止掉過頭去,好好看清楚真相。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 娜歐蜜‧克萊恩《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
|